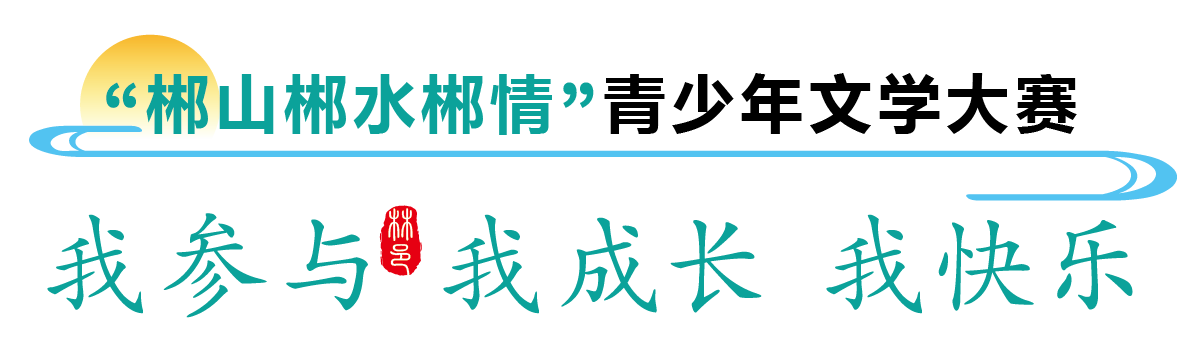贺晓溪
郴州市安仁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师
作者简介
贺晓溪,女,1991年7月出生,现任教于郴州市安仁县思源实验学校。任教期间撰写过多篇论文并获奖,同时也多次参加县级教学比武,被学校评为“最美教师”。
代表作品
一川风月,半城烟火
参赛作者:贺晓溪(郴州市安仁县思源实验学校)
漫过东江湖的水面时,木桨划开的不仅是粼粼波光,更是郴州把山水酿成生活的秘密。这座被南岭余脉温柔环抱的城,没有名山大川的张扬,却让郴江、苏仙岭、莽山这些寻常山水,长出了独有的烟火气与诗意——郴山不是沉默的背景,郴水并非无情的流逝,它们与市井人家的柴米油盐、古往今来的人文故事缠绕在一起,成了“郴情”最生动的注脚。
苏仙岭的晨光是被登山人的脚步声唤醒的。石阶上还沾着夜露,半山腰的“三绝碑”已迎来第一拨驻足者。秦少游被贬郴州时写下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”,字字是迁客的愁绪,却让郴江与郴山的羁绊,成了千年难解的题。可本地人从不纠结这“为谁而流”的怅惘,他们更爱在碑旁的石凳上摆开棋局,棋子落定的脆响,混着山间松涛与远处城区的早市吆喝,竟让碑文里的愁绪,生出了几分烟火暖意。山脚下的苏仙观,道士们晨练的太极招式刚柔并济,观前卖米饺的阿婆,竹篮里的米饺白胖滚圆,氤氲的热气漫过青石板路,与山间的云雾融在一起——苏仙岭的“仙”,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,而是山脚下一碗米饺的香,是登山人额头的汗,是碑文与生活的隔空对话。
若说苏仙岭藏着郴州的“闲”,那东江湖便盛着郴州的“灵”。每年四月到十月,拂晓的东江湖会被浓雾裹成一幅水墨画。渔夫撑着乌篷船,站在船头抛出渔网,银亮的网在空中划出弧线,瞬间被浓雾吞没,只留下渔网落水的“哗啦”声,和渔夫沙哑的吆喝,在水面上荡开圈圈涟漪。岸上的摄影爱好者们举着相机,屏气凝神地等待那“网落雾散”的瞬间,可往往等雾慢慢散去,露出的不是惊艳的光影,而是水面上漂浮的几片荷叶,或是远处农妇划着的小竹筏,竹筏上满载着刚采的莲蓬,翠绿的颜色把湖水都染透了。
我曾在雾散后跟着渔民去湖中心的小岛,岛上的人家靠着养鱼和种果树过活。女主人见我来,笑着递上一个刚摘的鹰嘴桃,桃子脆甜多汁,汁水顺着指尖滴在青石板上,竟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浅红。“这桃子啊,得靠东江湖的雾气养着,雾多的年份,果子就甜。”她一边说着,一边把刚晒好的鱼干收进竹筐,鱼干的咸香混着桃子的清甜,成了东江湖独有的味道。傍晚离开时,夕阳把湖水染成金红色,渔民们划着船唱着渔歌归来,歌声里没有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寂,只有“满载一船星辉”的踏实——东江湖的“灵”,从不是刻意营造的仙境,而是渔民手中的渔网,是岛上的桃李芬芳,是雾气与人间烟火的相拥。
莽山的性子,与苏仙岭的闲、东江湖的灵都不同。它藏在郴州的南端,像个倔强的守护者,把最原始的野性与温柔都锁在群山里。登莽山的路不好走,石阶常常被青苔覆盖,偶尔还会遇到窜过林间的小松鼠,抱着松果,眨着黑亮的眼睛打量路人。山顶的“鬼子寨”瀑布,水流从百米高的悬崖上倾泻而下,砸在岩石上,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,可瀑布旁的观景台旁,却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石碑,刻着当年红军路过莽山时,村民们送粮送水的故事。
去年深秋,我在莽山遇到一位守林人老李,他穿着褪色的迷彩服,背着装满野果的竹篓,说要带我去看“秘密”。跟着他钻进密林,走了半个多小时,眼前突然出现一片野生的红枫林,枫叶红得像火,把整片山谷都烧得滚烫。“这片枫林啊,没人知道有多少年了,我爷爷年轻时就常来这儿砍柴,现在轮到我守着,不让人乱砍,也不让人过度开发。”老李说着,从竹篓里拿出几个野柿子,递给我一个,“你尝尝,这是莽山自己长的,比城里买的甜。”柿子的甜里带着一丝涩,像极了莽山的性子——看似冷峻,藏着的却是化不开的温柔。下山时,老李指着远处的村庄说:“你看,山里的泉水流到村里,村民们就用它灌溉稻田,煮茶做饭。莽山不只是座山,是我们的饭碗,是娃们长大的地方。”
暮色降临时,我站在郴边的吊桥上,看着江水缓缓流过城区。江面上的灯光映着两岸的商铺,卖临武鸭的铺子飘出诱人的香气,穿汉服的姑娘们在江边拍照,笑声与江水的流淌声混在一起。远处的苏仙岭早已隐在夜色里,只有山顶的灯塔还亮着,像一只温柔的眼睛,注视着这座城。东江湖的雾气想必又起了,莽山的枫林在月光下该是另一番模样——郴州的山水,从不是孤立的风景,它们是苏仙岭下的米饺,是东江湖上的渔网,是莽山深处的野柿子,是本地人柴米油盐里的日常,是异乡人念念不忘的乡愁。
秦少游笔下“绕郴山”的郴江,终究是“流下潇湘去”了,可它流过的地方,早已把郴州的情意,酿成了一川风月,半城烟火。这座城的动人之处,从不是山水有多奇绝,而是山与水、人与景,早已长成了彼此的模样——郴山因郴水而灵秀,郴水因郴人而温暖,而这份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的牵连,便是“郴情”最动人的答案。
山水为笺,烟火作墨
参赛作者: 贺晓溪(郴州市安仁县思源实验学校)
郴州的山水,从不是挂在墙上的风景画。它藏在老艄公摇橹的水声里,裹在采药人竹篓的药香中,浸在草原牧民熬煮的奶茶里,以最朴素的姿态,把“郴情”写进每个寻常日子。若说别处的山水是用来“观赏”的,郴州的山水便是用来“过日子”的——山与水在这里不只是背景,而是与人心、与烟火、与岁月缠绕共生的伙伴。
便江渡:一船时光,半渡烟火
清晨的便江,是被渡船的“吱呀”声叫醒的。老艄公周伯的渡船泊在古渡口,船身的木纹里嵌着几十年的水汽,像老人脸上深嵌的皱纹。他总说:“这船比我儿子岁数都大,当年我爹撑它渡人,如今轮到我。”渡口的青石板被一代代人的脚步磨得发亮,石板缝里冒出的青苔,沾着晨露,像撒了一层碎钻。
我常趁晨雾未散时去乘渡船。周伯摇橹的动作缓而稳,木橹搅动江水,泛起的涟漪把两岸的竹林都揉成了模糊的绿影。船上常有去对岸赶集的村民,竹篮里装着刚摘的油茶果、自家做的蕨根糍粑,香气混着江风飘满船舱。有次,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指着江面喊:“周爷爷,你看!鱼在跳!”周伯停下橹,笑着指给她看:“那是鳜鱼,要往上游去产卵哩。”小姑娘伸手去够江水,指尖刚碰到水面,便被母亲轻轻拉住:“别闹,小心掉下去,周爷爷的船稳,可也经不住你晃。”
渡船行到江心时,周伯会从船舱里摸出一个陶制小壶,倒出两杯山茶。“这茶是对岸山上采的野茶,用便江水煮,才有这股清甜味。”他呷了一口,眼神望向远处的滩涂,“以前这江里有放排的人,几十根木头连在一起,顺流而下,号子声能传好几里地。现在不用放排了,木头走公路,可这江,还是要渡人。”说话间,晨雾渐渐散开,阳光洒在江面上,金闪闪的,像撒了一把碎金。岸边的芦苇丛里,几只白鹭突然飞起,翅膀划破水面的光影,美得让人舍不得眨眼。
靠岸时,赶集的村民陆续下船,周伯帮一位老奶奶拎起沉甸甸的竹篮,叮嘱道:“慢着点,石板滑。”老奶奶笑着应:“晓得了,你也早点收工,别让你家婶子等急了。”周伯摆摆手,又把橹摇了起来,渡船掉头时,船尾划出一道弯弯的水痕,像给江面系了个温柔的结。便江的水,就这样载着渡船、带着烟火,把两岸的日子,渡成了悠长的诗。
王仙岭:一溪药香,半山草木
午后的王仙岭,藏在浓得化不开的绿意里。山间的溪流顺着石阶往下淌,水清澈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,偶尔有几片落叶浮在水面,打着转儿往下游去。溪边常有采药人,背着竹篓,手里拿着小锄头,在草丛里仔细搜寻。张叔就是其中一位,他在这山里采药快三十年了,哪块石头下长着七叶一枝花,哪片坡上的鱼腥草最肥嫩,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。
我曾跟着张叔进山采药。他走得极慢,脚步很轻,像怕惊扰了山里的草木。“采药要讲规矩,”他一边拨开草丛,一边说,“只采成熟的,留着幼苗;只采一半,给山神留一半。不然,下次再来,就啥也找不到了。”说着,他蹲下身,用小锄头轻轻挖起一株带着露珠的石菖蒲,“这东西好,祛湿开窍,用它煮水喝,夏天不中暑。”他把石菖蒲放进竹篓,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,在上面记着什么。“这是采药日记,记着哪天采了啥,长在啥地方,以后子孙想采,也知道规矩。”
走到半山腰的竹林时,张叔突然停住脚步,指着一棵竹子说:“你看,这竹子上有个竹节虫,跟竹子一个颜色,不仔细看根本找不到。”我凑过去,果然看见一只绿色的虫子,趴在竹节上,一动不动,若不是张叔指给我看,我根本发现不了。“山里的生灵,都有自己的法子活下去,我们采药人,就是要懂它们,敬它们。”张叔说着,从竹篓里拿出一个野果,擦了擦递给我,“这是野猕猴桃,别看小,甜着呢。”我咬了一口,果肉酸甜多汁,带着阳光和草木的清香。
下山时,夕阳把竹林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张叔的竹篓已经半满,里面装着石菖蒲、鱼腥草、七叶一枝花,还有几株不知名的小草。“这些药,一部分自己用,一部分送给村里的老郎中,给乡亲们治病。”他说,“王仙岭的山,养活了我们一代代人,我们也要好好护着它。”溪边的水流得更欢了,带着药香,顺着山势往下淌,仿佛要把这半山的草木情,都送到山脚下的村庄里。
仰天湖:一甸草色,两袖风吟
黄昏的仰天湖,像一块铺在山间的绿绸缎。草原上的风车慢悠悠地转着,叶片划过夕阳的余晖,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牧民阿佳正坐在蒙古包前熬奶茶,铜壶在火上“咕嘟咕嘟”地响,奶香味混着酥油的气息,飘得很远。她的儿子小巴特尔,正骑着小马在草原上奔跑,小马的蹄子踏过青草,溅起一串串露珠。
“仰天湖的草,到了夏天就长得齐腰深,”阿佳一边搅着奶茶,一边说,“牛羊吃了这里的草,肉香,奶也甜。”她给我倒了一碗奶茶,茶汤呈浅褐色,喝一口,又香又醇,带着淡淡的咸。“这奶茶要用湖边长的野茶煮,再加上本地的牦牛奶,才有这味道。”阿佳指着远处的湖面,“你看,那湖里的水,是山上的雪水融化来的,干净得很,我们喝的水、浇地的水,都靠它。”
说话间,小巴特尔骑着小马回来了,手里拿着一束野花,递给阿佳:“阿妈,你看,好看不?”阿佳接过花,插在蒙古包门口的陶罐里,笑着说:“好看,我们巴特尔眼光好。”草原上的风渐渐大了,吹动着阿佳的头巾,也吹动着远处的经幡。夕阳把阿佳和小巴特尔的影子拉得很长,与风车的影子交叠在一起,像一幅流动的画。
我问阿佳,在这里住了多久。“我嫁过来快二十年了,”她说,“以前这里的路不好走,外面的人很少来。现在修了路,来旅游的人多了,我们也开了蒙古包民宿,日子越过越好。但我们有规矩,游客来了,只让他们在指定的地方玩,不能踩坏草场,不能往湖里扔垃圾。这草原和湖,是我们的根,得护好。”
暮色渐浓时,草原上亮起了星星。阿佳点燃了蒙古包前的篝火,火光映着大家的笑脸。牧民们拉起手,围着篝火唱起了歌谣,歌声在草原上回荡,与风车的转动声、湖水的流淌声,汇成了最动听的旋律。仰天湖的草原,就这样用青草、用湖水、用牧民的歌声,把日子过成了诗。
夜深时,我站在仰天湖边,看着天上的星星倒映在湖里,像撒了一湖的碎钻。远处的风车还在慢悠悠地转着,仿佛在诉说着这里的故事。郴州的山水,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——便江的渡船连着两岸的烟火,王仙岭的溪流载着草木的深情,仰天湖的草原牵着牧民的期盼。它们以山为骨,以水为脉,以情为魂,把“郴情”写进每一寸土地,写进每个人的心里。这,就是郴州的山水,是让人来了就不想走,走了还会念的地方。
烟火织就的山水诗行
参赛作者:贺晓溪(郴州市安仁县思源实验学校)
郴州的山水,从不是孤悬天地间的风景标本。它是郴江里摇橹人溅起的水花,是五盖山茶园里沾着晨露的嫩芽,是西河湿地边护鸟人手中的望远镜——山与水在这里,早已和人的日子拧成了一股绳,把“郴情”酿成了可触可闻的烟火气。若说别处的山水是供人仰望的画卷,郴州的山水便是让人扎进其中的生活本身,每一步踏下去,都能踩出草木与人间的共鸣。
裕后街:古桥映水,早市藏情
清晨的郴江,是被裕后街的石板路叫醒的。沿江而建的老街,青石板缝里还嵌着昨夜的雨珠,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,像在和江水流淌的“哗哗”声唱和。街口的古桥,桥墩上爬满了青苔,桥栏被一代代人的手掌磨得光滑,桥头卖艾草粑粑的李阿婆,竹筐刚摆开,热气就顺着竹篾的缝隙往上冒,混着江风里的水汽,在桥洞下绕出一圈圈白蒙蒙的雾。
“阿婆,来两个粑粑!”穿校服的小姑娘蹦跳着跑过来,书包上的铃铛叮当作响。李阿婆笑着应着,用竹夹夹起两个冒着热气的粑粑,油纸袋上印着小小的“郴”字。“慢点吃,刚出锅烫嘴哩。”她看着小姑娘跑远的背影,又转头望向江面——老船工周师傅正摇着小木船,船头放着刚从江里捞的水草,要送去上游的湿地公园。“周哥,今天江里水凉不?”李阿婆朝江面喊。周师傅停下橹,笑着回:“凉哩,但鱼多!中午给你送两条新鲜的!”
我常坐在桥边的石阶上看早市。卖菜的农户挑着担子从桥上走过,竹筐里的青菜还沾着泥土,茄子紫得发亮,辣椒红得像火;修鞋的老师傅坐在巷口,手里的锥子穿针引线,时不时抬头和路过的老街坊打招呼;穿汉服的姑娘们举着油纸伞,裙摆扫过青石板,与背着竹篓的采药人擦肩而过——古桥连着江,江连着街,街上的人连着彼此,郴江的水就这样,把老街的烟火气,揉成了一碗温热的艾草粑粑,一口下去,全是过日子的踏实。
五盖山:云雾煮茶,竹影摇风
正午的五盖山,总被云雾裹得半遮半掩。山间的茶园顺着山势铺展开,茶树矮矮的,叶片上沾着露珠,阳光透过云雾洒下来,在茶叶上镀上一层淡淡的金。茶农陈叔戴着斗笠,背着竹篓,手指在茶树间灵活地翻飞,采下的嫩芽放进篓里,凑成一小捧翠绿。“采茶要趁雾没散,这时的芽最嫩,炒出来的茶才有兰花香。”他一边采,一边和我说话,声音里带着山里人的爽朗。
跟着陈叔到山腰的茶厂,土灶上的铁锅已经烧得发红。他把采来的嫩芽倒进锅里,双手快速翻炒,茶叶在铁锅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香气瞬间漫了出来,混着灶膛里柴火的烟味,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“这茶叫‘五盖山云雾茶’,得用山泉水煮,才能出真味。”陈叔说着,从水缸里舀出一勺泉水,倒进陶壶,放在炭火上煮。水开时,陶壶“咕嘟咕嘟”地响,他提起壶,将热水冲进放好茶叶的盖碗,茶汤先浅后深,慢慢变成透亮的黄绿色,杯口飘着的雾气,与山间的云雾融在了一起。
喝着茶,陈叔指着远处的竹林说:“那片竹林,是我爷爷种的,现在成了竹编艺人的宝库。”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,几个竹编师傅正坐在竹林边,手里的竹子在指尖翻飞,不一会儿就编出半个竹篮。“山里的东西,不能光靠拿,得会养。”陈叔说,“茶树要修枝,竹林要间伐,泉水要护着,这样山里的好东西,才能一代代传下去。”说话间,一阵风吹过茶园,茶树叶子轻轻摇晃,竹影在地上晃出细碎的光斑,云雾在山间慢慢游走,五盖山的日子,就这样浸在茶香与竹影里,慢得像一首没唱完的山歌。
西河湿地:夕照归鸟,草木含情
黄昏的西河湿地,是被候鸟的翅膀擦亮的。夕阳把河面染成橘红色,芦苇荡在风中轻轻摇曳,偶尔有几只白鹭从水面掠过,翅膀划破波光,留下一道道细长的水痕。护鸟人老张背着望远镜,沿着河岸慢慢走着,裤脚沾满了草籽。“这几天,南迁的候鸟开始来了,得盯着点,别让有人来掏鸟蛋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举起望远镜,镜片里映着远处一群正在水面嬉戏的野鸭。
我跟着老张走到湿地深处的观鸟台,木质的台子上刻着各种候鸟的名字和画像。“你看,那是斑嘴鸭,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来这儿歇脚;那边飞得高的,是白琵鹭,嘴巴像把小勺子,专门捞水里的小鱼吃。”老张指着远处,语气里满是骄傲,“以前这湿地没人管,垃圾多,候鸟也少。现在好了,大家都知道护着这儿,水里的鱼多了,鸟也越来越多,连城里的人都爱来这儿散步。”
说话间,几个孩子笑着跑过来,手里拿着画纸和彩笔,要画夕阳下的候鸟。“张爷爷,今天能看到白鹤吗?”一个小男孩仰着头问。老张笑着摸了摸他的头:“快了,再过几天,白鹤就会来啦。”孩子们趴在观鸟台上,认真地画着,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与芦苇的影子交叠在一起。远处的城市亮起了灯光,晚风吹过湿地,带着草木的清香,候鸟的鸣叫声从远处传来,与孩子们的笑声混在一起——西河湿地的黄昏,就这样被归鸟、草木和人的温柔,酿成了一首安静的诗。
夜深时,我站在西河岸边,看着远处的灯光倒映在水里,像撒了一河的星星。老张说,湿地的夜最静,能听到草叶生长的声音,能看到萤火虫在芦苇丛里飞。郴州的山水,从来都不是冰冷的风景——裕后街的古桥连着人间烟火,五盖山的云雾煮着岁月悠长,西河湿地的草木守着生灵相依。山给人以滋养,水给人以温柔,人给山水以深情,这份“你护我长大,我陪你变老”的牵连,便是“郴情”最动人的模样,也是郴州山水最鲜活的诗行。
作品点评
《一川风月,半城烟火》这篇散文以 “郴情” 为魂,串联起苏仙岭、东江湖、莽山的景致与烟火。从三绝碑旁的棋局、米饺香,到雾中渔网、岛上桃甜,再到莽山红枫、守林人野柿,将山水与人文、市井相融。文笔灵动如郴水,于细节处见真章,让 “山与水、人与景共生” 的郴州情意,浸润纸间,绵长动人。
《山水为笺,烟火作墨》此文以 “山水过日子” 为核心,串联便江渡、王仙岭、仰天湖三地烟火。老艄公的渡船、采药人的竹篓、牧民的奶茶,让山水成为生活的参与者。笔触细腻如便江水,于橹声、药香、歌声中,写尽山水与人心的共生羁绊,“郴情” 便在这烟火浸润里愈发真切动人。。
《烟火织就的山水诗行》此文以 “山水即生活” 为脉络,串起裕后街、五盖山、西河湿地的烟火与温情。古桥边的艾草香、茶园里的炒茶声、湿地中的护鸟语,让山水与人的羁绊具象可感。文笔温润如郴江水流,于细节处勾勒出 “山养人、人护山” 的共生图景,“郴情” 便在这草木与人间的共鸣里愈发绵长。
编辑提示
文学创作是一场精益求精的修行,难免存在疏漏。若您在阅读中发现错字、语病、逻辑或抄袭问题,又或是作者自身想要修改完善作品,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您的每一条反馈,都是帮助作品日臻完美的珍贵助力,期待与您共筑优质内容。
编辑:王 君
二审:张振萍
三审:李艳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