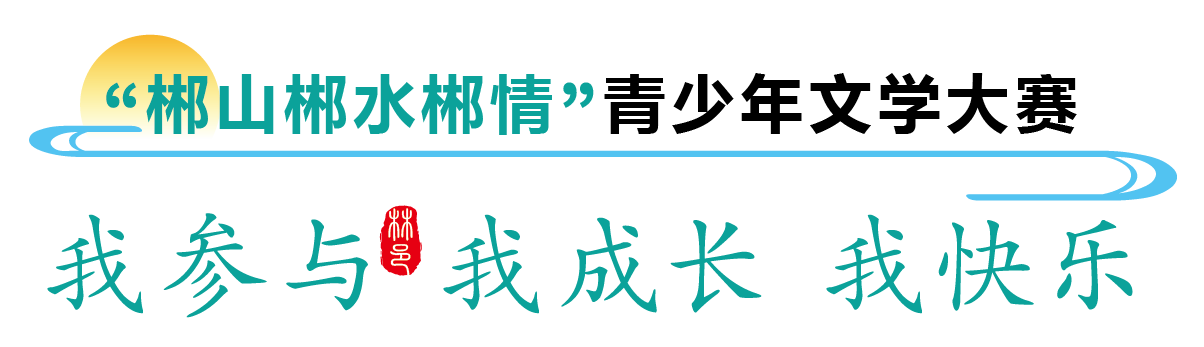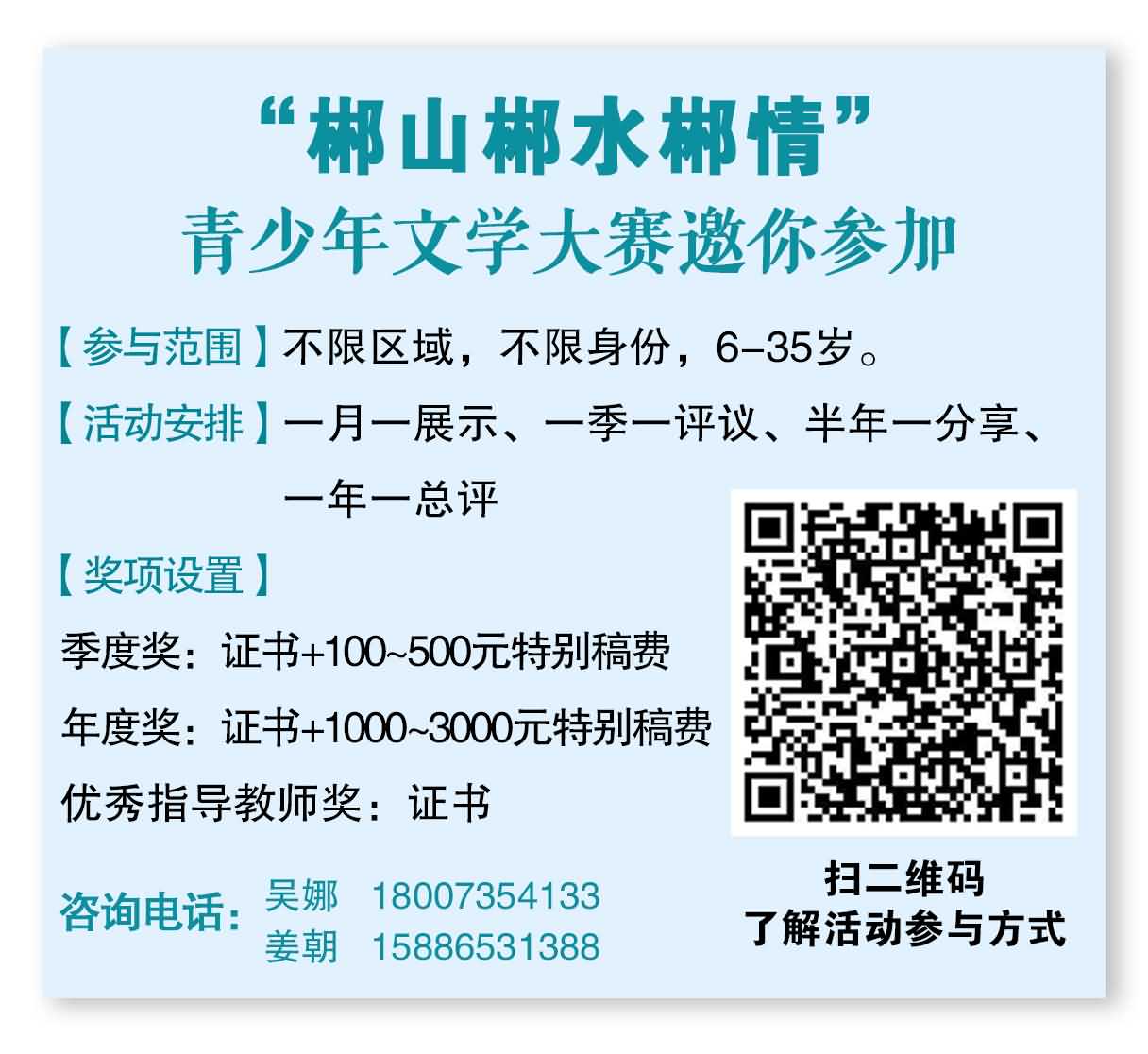吕贻婷
郴州市桂阳县莲塘镇光明中心学校教师
作者简介
吕贻婷,女,1999年1月出生,现任教于郴州市桂阳县莲塘镇光明中心学校。
创作背景:这篇作文源于作者对湘南临武地区矿业遗产的观察。通过描绘三十六湾矿区伤痕与生机并存的景象,试图探索超越传统审美的自然定义,反思工业开发与生态修复的永恒命题。
代表作品
三十六湾的缄默与回响
参赛作者:吕贻婷(郴州市桂阳县莲塘镇光明中心学校)
晨雾如纱,轻覆在临武古城之上。我立于东塔之巅,看武水河蜿蜒如带,将千年的故事静静流淌。这座湘南小城,在多数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墨点,然而当我真正深入它的肌理,却发现每一寸土地都暗藏着地质年轮与人文密码交织的深邃。此行,我欲寻访的并非那些明信片式的风景,而是一个藏在群山褶皱里的地名——三十六湾。父亲曾说,那里藏着临武的另一副面孔。
去三十六湾的路,早已废弃多年。向导是位沉默的老矿工,他的脊背弯成一道沉重的弧线,仿佛仍背负着过往岁月里那些不可见的矿篓。我们的车在几乎被野草吞没的土路上颠簸,两旁是触目惊心的矿洞,像大地上无数沉默的伤疤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寂静,没有鸟鸣,甚至没有风穿过林梢的沙沙声。这里的美,是一种被彻底撕裂后又顽强愈合的、带着剧痛的美。
老矿工停在一片狼藉的矿渣堆前,黝黑的手指向远方。顺着他所指,我看见匪夷所思的一幕:赭红色的矿渣堆上,竟星星点点地盛开着一种纯白的小花,花瓣薄如蝉翼,在稀薄的空气中艰难而骄傲地舒展。更远处,一湾被矿物质染成蔚蓝色的积水,宛如巨兽凝视苍天的独眼,冰冷,深邃,美得令人心悸,也荒凉得让人脊背发凉。“这叫矿山勿忘我。”老矿工的声音粗粝如砂纸,“矿没了,人走了,它倒活下来了。”
我们终于抵达三十六湾的核心。巨大的采选矿设备锈迹斑斑,以各种扭曲的姿势凝固在原地,像史前巨兽的化石,诉说着一个狂热时代的喧嚣与贪婪。然而,就在这“钢铁坟场”的缝隙里,自然正以惊人的力量 reclaim(夺回)它的失地。藤蔓缠绕着破碎的传送带,野草从齿轮间蓬勃生长。毁灭与生机,荒芜与灵动,在此处完成了惊心动魄的共生。我忽然懂得了父亲的话——这里的景色不是用来观赏的,是用来阅读的。每一页都写满了资本的灼热、劳动的汗血、自然的悲鸣与复苏的坚韧。
下山时,老矿工的话匣子终于打开。他谈起昔日三十六湾的“繁华”,夜晚的赌场与酒馆人声鼎沸,赌徒们用沾着矿粉的钞票拍桌;谈起来自地下深处的恐惧与兄弟间的义气;谈起儿子这一代无人再愿回到这里,只有他们这些老骨头,还会时不时上山看看。他的叙述里没有怀念,也没有憎恶,只有一种巨大的、近乎神圣的平静。“人从地里掏东西,掏得太狠了,地就会疼。地一疼,人就得走。现在地不疼了,睡熟了。”他喃喃道。
黄昏时分,我独坐于一处僻静的山湾。夕阳给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镀上了一种悲壮的柔光。万籁俱寂中,我仿佛听见了各种声音:当年开山炮的隆隆轰鸣、矿工的号子、银行的点钞声、生态哀鸣的断裂声,以及眼下,清风拂过白色小花的微弱颤音。所有这些,共同谱成了一曲三十六湾的缄默交响。
临武的景色,在东塔的悠远、武水的温婉之外,原来还有三十六湾这般惊心动魄的篇章。它绝非恬静的田园诗,而是一部用土地血肉写就的宏大叙事,关于索取与馈赠,毁灭与救赎。它教会我的,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审美:美,并非总是和谐与完满的代名词。真正的壮丽,足以包容断裂层的狰厉,接纳伤痕本身的深邃。那朵开在矿渣之上的白色小花,其生命力远比开在精致花园里的玫瑰更撼人心魄——因为它见证过地狱,却依然选择了绽放。
当我转身离开,将三十六湾的缄默还给群山,我知道,我已将临武最沉重、最辉煌的景色,烙在了心上。那是一片土地袒露的最真实的肌肤,它在无声诉说:看吧,记住吧,这就是我们来时的路,而路的前方,唯有与万物温柔共生,方能走向真正的黎明。
作品点评
文章以寻访临武三十六湾为线,借废弃矿洞、矿山勿忘我、锈迹设备等意象,勾勒土地的伤痕与生机。老矿工的叙述添历史厚重,将自然复苏与人类过往交织,解构“美”的定义。文字深沉有力,于悲壮中见哲思,尽显对土地的敬畏与反思,感染力强。
编辑提示
文学创作是一场精益求精的修行,难免存在疏漏。若您在阅读中发现错字、语病、逻辑或抄袭问题,又或是作者自身想要修改完善作品,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您的每一条反馈,都是帮助作品日臻完美的珍贵助力,期待与您共筑优质内容。
编辑:王 君
二审:张振萍
三审:李艳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