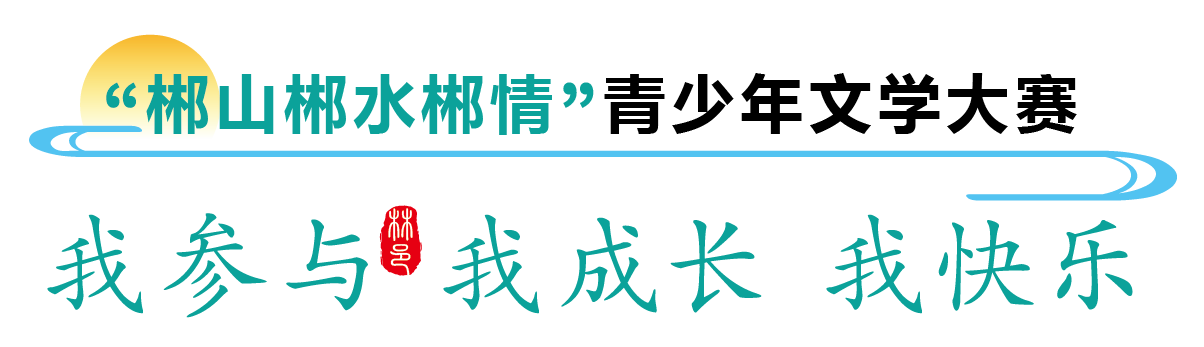朱盈盈
郴州市第五中学学生
作者简介
朱盈盈,女,2011年11月出生,就读于郴州市第五中学。会画画,也能弹奏各种乐器。
创作背景:闲暇时,作者常听长辈讲述家乡的故事,看着郴州越变越美,心中满是对先辈付出的感恩。用笔墨写下郴州的美,为建设更美的郴州添一分光。
代表作品
藏在郴城里的细碎情深
参赛作者:朱盈盈(郴州市第五中学)
指导老师:赵李宣(郴州市第五中学)
晨光熹微时,薄雾便给郴江笼上半透明的纱衣,像天工用云絮织就的晨裳。岸边垂落的柳丝沾了雾的软,柳枝轻触水面,荡漾着层层水波涟漪;芦苇穗裹着露珠,风一吹便簌簌落进江里,惊起两三尾细鱼,摆着银鳞钻进深处。我沿着江岸慢慢走,青石板缝里还沁着郴江的湿润,一丝凉意从鞋底悄然爬上,轻轻环住脚踝,又漫到裤脚边,带着水特有的清润气息,连呼吸都似沾了水汽的甜。
郴江蜿蜒着连通东江湖,这水是活的,是淌在郴州人日子里的血脉。开春时节,江水悄悄漫过滩涂,裹着岸柳新发的嫩黄芽尖气儿,慢悠悠地淌。风过时,水面皱起细碎的纹,把岸边的绿影揉成晃动的山水画;待阳光爬高,江面顿时碎金闪烁,像天女不小心打翻了银匣,银屑细碎落满水面,随着水波轻轻起舞。偶有麻雀大小的水鸟贴着江面掠过,轻点水面,溅起星子似的水花,而后扑棱棱振翅而去,留下的涟漪一圈圈淡开,反倒衬得江水更显柔婉。到了盛夏,东江湖的晨雾更浓,渔船从雾里钻出来时,木桨划水的“哗啦”声先于船影传来,渔民站在船头,渔网一扬便撒开片浅棕的云网,落进水里时,连雾都似被惊动,这样良辰美景,我不由得屏住呼吸。
郴州人的生计,从来离不开这湾活水。天刚亮,老渔人王伯就驾着竹筏破开水面,竹篙轻点河岸,筏子便顺着水流漂。他手臂一扬,渔网带着风的劲儿哗然入水,网绳在手里绕两圈,待稍停片刻,再慢慢往上拉——网兜里顿时银鳞跃动,白条鱼、鲫鱼挤在一起,尾巴拍打着网眼,溅出的水珠落在河里,又融进这汪活水中。王伯把鱼放进竹篓,水顺着篓缝滴滴答答落回河里,他笑着跟岸边晨练的老人打招呼:“今儿鱼肥,回家给孙娃熬汤正好!”郴江静静流淌,把郴州人勤劳的烟火气,一点点浸润进每个人的心田:江边洗衣的妇人捶打衣裳,皂角泡沫顺着水流漂;孩童拎着小网在浅滩追鱼,笑声落进水里,惊起更多细碎的涟漪。
郴州人的情意,藏在莽山的石阶与山花之间。山间蜿蜒的石阶,是二十多年前乡亲们一锤一凿铺就的。那时没有机械,男人们凌晨就背着水泥袋上山,腰上系着绳索,一步一步往陡坡挪;女人们则提着水壶、揣着红薯,在中途的石台上等着,见人上来就递水擦汗。多少汗水渗进石缝,才铺就这通向外头的路。护林员老李守了莽山十年,日日巡山时,见到被风吹折的枝丫,便弯腰小心移到路边,怕绊着游客;遇见迷路的旅人,他总笑着指方向:“顺着杜鹃花走,再拐两个弯就能到山顶!”春日杜鹃盛放时,他还会揣着小剪刀,修剪过密的花枝:“要让每朵花都好好开放,让每个人都看见莽山的美。”有次我遇见他,他正蹲在一株刚冒芽的杜鹃旁,用指尖把压住新芽的落叶拨开,指尖沾着泥,眼里却亮得像盛着光。
傍晚离开时,郴江的雾早已散了,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,王伯的竹筏泊在岸边,渔网晾在船头,随风轻轻晃。此刻,莽山的轮廓浸在暮色里,山顶的杜鹃似还留着白日的艳色。我忽然懂了,郴山默然,每一块石头雕刻着乡民的守护;郴水潺潺,每一片波纹载着郴州人的热忱。这份藏在郴城山水里的“郴情”,无需华丽辞藻,却比任何风景都动人——正是这份情,让郴州这座福城,永远洋溢着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。
郴江边的老味道
参赛作者:朱盈盈(郴州市第五中学)
指导老师:赵李宣(郴州市第五中学)
郴州的魂是藏在它的清晨和傍晚里的。那天清晨,我不是醒来的,是被一股熟悉又陌生的、湿漉漉的水汽给缓缓将我从梦中牵出。连着考了好几天试,心里闷得发慌,干脆蹬上运动鞋,去江边溜达溜达,把心里的愁绪散散。
五月的郴江,是刚睡醒的。雾不是纱衣,倒像是它呼出的一口气,一缕缕地萦绕在江面上,缠在岸边的老柳树上。柳枝低低地垂在江面,时不时探进水里,划一下,又缩回来,像个在耍水的调皮孩子。脚下的石板路坑坑洼洼,缝隙里沁着隔夜的凉气,踩上去,脚心一下就略过清凉,人瞬间清醒了。几只早起的白鹭在浅水处踱步,长腿细得像枯树的枝干,每走一步,水面就荡开一圈细细的波纹。
江心有条小竹筏,船上的人隐在雾气当中我看不清,但那动作如此熟悉——是爷爷的老朋友,旺喜伯。他撒网不像表演,像在跟水打交道。黝黑的胳膊一抡,网“唰”地一声飞出去,像抖开一件巨大的蓑衣,平平地铺在水面上,然后咕咕地沉下去。他撒网从不看时间,眯着眼抽了根烟的工夫,就开始不紧不慢地收网。渔网线嵌进他黝黑的胳膊里,肌肉紧绷着,像老树的枝干。拉上来时,网里白光闪闪,都是些活蹦乱跳的小白凌。他看见岸上的我,手挥了挥,手腕上那根褪了色的红绳,在朦胧的水汽里晃荡着,虽说褪了色却看得是那么真切。
我沿着江岸漫步,拐角处就是旺喜伯家的“老地方鱼粉店“。店门口支着一口深不见底的大铁锅,旺喜婶系着沾满油渍的围裙,正把刚送来的鲜鱼倒进翻滚的奶白色高汤里。那股味道猛地冲过来,是胡椒的辛、鱼肉的鲜、和大火熬出的骨香搅在一起,撬开所有人的嗅觉钻了进来。这味道,就是我小时的早晨。小时候爷爷总带我来这儿吃这喷香的鱼粉
“小姑娘,今日难得有空!”旺喜婶嗓门亮,一边舀汤一边喊我,“听说你前几天考试咧?考得么子样?还是老样子?要宽粉?“我点头坐下,塑料凳子腿有些晃动,发出吱呀的响声。
旁边陈旧日的木桌上,放着旺喜伯的|日收音机,唱着听不清词的采茶戏,电流声是如此杂乱的,却让人觉得莫名安心。阳光这时才真正拨开云雾,照在店门口经无数次踩踏磨得光滑的石阶上,亮晶晶的,像一块流传千年的古玉。几个老邻居坐在一旁,端着瓷碗,嗦溜着粉,偶尔抬头聊几句家里事儿,虽说都是些柴米油盐的琐事,却透着股熟悉劲。
我捧起碗,热气瞬间模糊了眼镜片。我摘下眼镜,吹开油花,小心地喝了一口汤。滚烫鲜辣的汤汁顺着喉咙滑下去,那热气把心中那忧郁化开了。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,后背也渐渐湿了,却觉得舒畅无比。
就在这时,我看见旺喜伯提着鱼桶回来了。他和旺喜婶低声说了几句什么,旺喜婶便从桶里捞起一条最大的鱼,利落地去鳞、剁成鱼块,下进另一个小锅里。不一会儿,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鱼肉汤走过来,放在我面前:“专门给你做的,考试费脑子,可要好好补补。你老伯今早打到条大鱼,少见得嘞!
我望着那碗奶白色的鱼汤,再看看旺喜伯那双被水泡得发白起皱的手,鼻头有些发酸。我忽然明白了——所谓“郴情”,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东西。它是这片雾,是这碗滚烫的粉,是旺喜伯那双泡白的双手,是旺喜婶无微不至的关照,是这条流淌了千百年却依然温润的郴江。它流淌进每个郴州人的血脉,住在每一天最平凡的生活里。如今,它也顺着江水的氤氲飘来,长成了我味觉记忆中最深的一笔,如一簇扎根心底、再拔不掉的青青草。
它从来不需要被说出,它只需要被记得。记得在每个清晨黄昏,在每一个朴素却温暖的日子里,被这样轻柔地惦记着、呵护着。这就是郴山郴水给予我的,最平凡却也最深刻的人间真情。
作品点评
作文开篇以晨雾郴江入画,青石板的凉意、柳丝的软嫩,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清润的地域质感;继而借东江湖的碎金波光、渔人撒网的日常,让“水之活”与“人之勤”自然交融。莽山石阶的来历、护林员老李的细节,皆是郴州人对故土的深情。全文以晨始、以暮终,结构圆融,语言如郴水般柔婉却有力量,真正做到了“山水藏情,情入人心”,读来满是烟火暖意与乡土眷恋。
编辑提示
文学创作是一场精益求精的修行,难免存在疏漏。若您在阅读中发现错字、语病、逻辑或抄袭问题,又或是作者自身想要修改完善作品,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您的每一条反馈,都是帮助作品日臻完美的珍贵助力,期待与您共筑优质内容。
编辑:黄萍
二审:刘娟丽
三审:李艳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