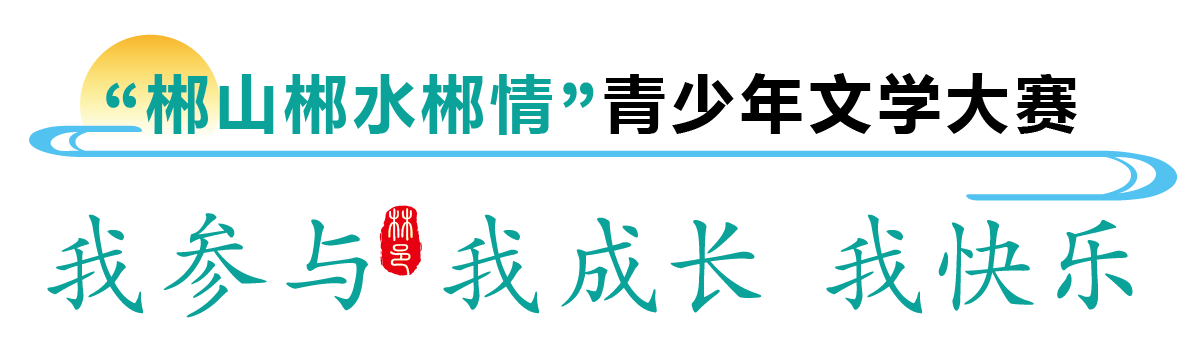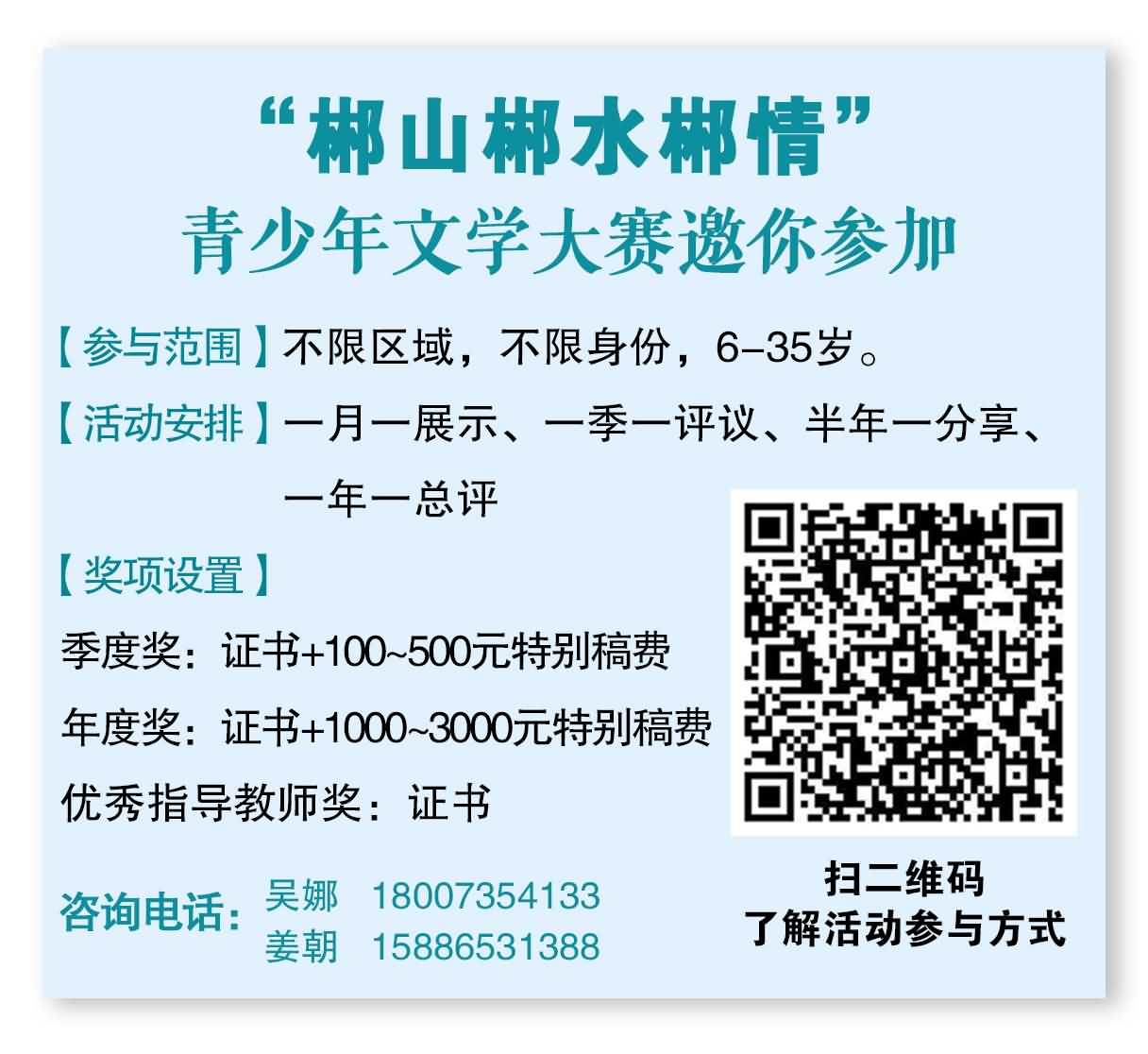黄梓轩
郴州市桂东县沤江镇增口九年制学校学生
作者简介
黄梓轩,女,2011年11月出生,就读于郴州市桂东县沤江镇增口九年制学校七年级,热爱阅读、写作,喜欢观察事物,被评为“书香少年”。
创作背景:有时我总疑心故乡是上帝打翻的调色板,虽五颜六色却独一无二!家乡的每一片土地都是我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!
代表作品
郴字为印,山水为魂——我独一无二的家乡
参赛作者:黄梓轩(郴州市桂东县沤江镇增口九年制学校)
指导老师:何金梅(郴州市桂东县沤江镇增口九年制学校)
“郴”这一字,组不了其他的词,它只属于郴州。当独一无二的字选择了独一无二的城,郴州怎能不别致?它柔情在水墨丹青里,是“人间天上一湖水,万千景象在其中”的雾漫小东江;它璀璨在文化肌理中,是“叉鱼春岸阔,此兴在中宵”的北湖雅韵,是裕后街华灯初上时的绰约身姿;它高洁在莲影波光间,是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爱莲湖;它壮丽在丹霞画卷上,它霸气在天工造物处。一期一会,一字一城,我的家乡郴州,本就是这般独一无二。
郴州的山,是刻在大地的诗行。晨雾还没散尽时,高椅岭的红岩已开始发烫。连绵的岭脊像神龙俯卧,赤褐色的山脊似被太阳吻过的脊背,这是郴州递给天地的烫金名片,用丹霞的红与湖水的绿,写满了亿万年的时光密码。沿石阶上行,脚下的岩石带着粗粝的温度,数百米的山脊窄得仅容一人通行,两侧是近百米的悬崖,崖底的湖水绿得发蓝,像巨龙半睁的眼。风从耳边掠过,裹着湖水的潮气,恍惚间真能听见龙鳞摩擦的细碎声响。夕阳西沉时,整座山浸在蜜色的光里,回望龙脊在暮色中渐成暗褐,唯有水洼还亮着,盛着最后一缕天光。原来所谓奇观,从不是天生的完美,而是山懂等待,水懂包容,人懂珍惜——当亿万年的红岩遇见澄澈的水,当伤痕累累的土地遇见温柔的时光,便酿成了这杯独一无二的酒,醉了风,也醉了归人。
郴州的水,是流在心底的词韵。人说“不见东江湖,不知山水美”,晨雾漫过湖面的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。船桨划破水面的声响像声轻叹,惊醒了沉睡的丹霞,它们的影子在雾里慢慢舒展,恍若水墨画被雨水洇开了边角。雾是东江湖的诗,我坐在岸边石阶上,看它漫过脚踝,凉丝丝的潮气混着水草的腥甜,像刚启封的陈年酒坛。鸟雀从雾中钻出来,翅膀带起的水珠落在水面,漾开一圈圈涟漪,把雾的影子揉成细碎的光斑——原来雾从不是静止的留白,而是东江湖写给蓝天的信,用最温柔的笔触,写尽山水的缠绵。
郴江的水总带着几分缠绵。我曾在爱莲湖听雨,雨打荷叶的脆响,混着远处古戏台隐约的昆曲唱腔,竟分不清是雨丝缠上了水袖,还是戏文里的悲欢浸湿了眉头。湘南民居的飞檐上,瑞兽在雨雾中半隐半现,像守护着一方水土的记忆,把岁月的故事都藏进了青砖黛瓦的褶皱里。
最难忘东江湖的晨雾里,渔翁划着木船穿行,竹篙轻点,便搅散了满湖缥缈。雾散时,两岸丹霞层层叠叠,如摊开的历史册页。当地老人说,每块红石头里都藏着故事:有神农氏尝百草的足迹,有徐霞客探幽的墨痕,还有寻常人家灶台上飘起的烟火气。郴江依旧绕着郴山流,我忽然懂了,它流向的从不是潇湘,而是每个与这片土地相遇过的人,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这大概就是郴州吧——山是诗的骨架,水是词的韵脚,而人是让诗句活起来的平仄。关于它,我还有说不完的话:白露塘的杀猪粉,骨汤熬得奶白,码上现切的猪肉、猪血,撒把葱花,热辣辣一碗下肚,汗珠冒出来,浑身都熨帖;五里堆的烧鸡公,红辣椒在热油里翻滚,麻香裹着肉香,辣得人直咂嘴却停不下筷;还有那碗鱼粉,鲜辣的汤裹着滑嫩的粉,吃了一碗总想着下一碗。
这不是魔法,是独属于我的,独一无二的家乡郴州。
桂东草山:绿毯承雾,雾吻草绒
“敕勒川,阴山下,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每当念起这首北朝民歌,总觉那片辽阔草原远在千里之外,直到踏足桂东草山,才惊觉此处的绿与雾,早已将天苍苍野茫茫的苍茫,悄悄揉进江南的灵秀骨里。桂东的草山,是天地铺开的绿绒毯,雾是游走其间的精灵,在“雾锁山头山锁雾”的缠绵里,草与雾相依相偎,把整座山酿成了一坛浸着清露的酒,醉了四季,也醉了每个踏足的人。
草是绿毯的底色,以四季为笔晕染出万千姿态,恰如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的生生不息。春末的草带着初生的怯生生的嫩,鹅黄的叶尖卷着未展的芽,像刚睡醒的孩童蜷着小胖手。踩上去像陷进晒暖的棉絮里,脚底板酥酥的,指尖一碰,草尖的露水便顺着指缝溜开,留下沁骨的凉——那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清冽,全凝在这草尖上了。盛夏的草是泼翻的绿,齐膝深的草丛里藏着满当当的热闹:蒲公英举着白绒球等风来,像一群揣着远行梦的小伞兵;紫色野豆花串成串,晃出细碎的响,风过时像谁在轻轻摇着银铃,应和着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诗意;狗尾草最是调皮,趁人走过就悄悄把草籽粘在裤脚,要跟着去远方看看,活脱脱一群爱缠人的顽童。深秋的草染上焦糖色,茎秆却依旧挺直,风过时整片山都在沙沙低语,像在说疾风知劲草的道理。蹲下来能摸到叶片边缘的细齿,带着阳光烤过的干燥,那是经了岁月的倔强——宛如饱经风霜的老者,脸上刻着皱纹,脊梁骨却依旧硬朗。
雾是草山的纱衣,以晨昏为轴变幻出百种风情,正合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的朦胧之美。天刚破晓时,雾是从山谷深处漫出来的,稠得像刚熬好的奶,黏黏地裹着草尖,又似腾云似涌烟,密雨如散丝的缠绵。它先在草甸低处打个滚,把脚踝高的草尖浸成深绿,再慢悠悠爬上灌木丛,让枝桠挂满水晶似的水珠。远看像丛丛缀满碎钻的珊瑚,又若玉树琼枝作烟萝的幻境,伸手一碰,水珠叮咚落进草里,惊起一只跳蛛。等太阳爬到东山顶,雾忽然就轻了,一缕缕在草坡上飘,像谁裁了素纱在风里晾:有时聚成一团,把远处的风车藏进白茫茫里,只剩叶片尖在雾中摇晃,像巨人在雾里招手;有时散成薄纱,贴在草叶上,人走过时,雾就从衣襟边溜过,带着草木的清香,深吸一口,肺腑都像被洗过,恍若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的清润。站在山巅看雾流动才最妙,它从东谷涌向西坡,遇着岩石就绕个弯,像懂礼的访客;见了野花便停一停,像在轻轻吻每片花瓣,温柔得如同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的恋人。
草与雾的相遇,是自然写就的最美诗行,道尽青山看不厌,流水趣何长的相依相惜。雾散时,草叶上的水珠正映着阳光闪光,风一过就簌簌落,像撒了一地碎星;远处山峦露出青黛色轮廓,草山又变回坦荡的绿,宛如平芜尽处是春山的辽阔。这时才懂,桂东草山的动人,从不是草独自的繁茂,也不是雾单有的灵动:草是大地写的诗,以野火烧不尽的韧劲儿写下执着;雾是天空说的情话,以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写下缠绵;而当诗遇上情话,便有了这一步一景,一景一诗的画卷,让每寸土地都成了活着的诗,读不尽,也品不够。
终究,草还是那片草,雾还是那缕雾,却在绿毯承雾,雾吻草绒的轮回里,把桂东的山岗,酿成了比风吹草低见牛羊更添几分朦胧的人间仙境。离去时,衣角早沾了草籽,发间凝着雾珠,抬手一拂,满手都是草山的清。才明白这方土地早已把《敕勒川》的辽阔与江南的婉约,织成了记忆里拆不散的诗——风吹过,草还在摇,雾还在飘,而那份醉人的绿与朦胧,会永远留在心头,像一首哼不完的歌。
作品点评
这篇作文以“郴”字的独一性为切入点,巧妙串联起郴州的山水、文化与烟火,构思精巧。写山则绘高椅岭红岩如龙,写水则描东江湖雾似信,引诗句入景,让丹霞、雾江皆有了生命。从山水之景到爱莲湖听雨、古戏台唱腔,再到杀猪粉、烧鸡公的烟火气,由景及情,从雅致到市井,层次分明。语言兼具诗意与鲜活,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的珍视与热爱,将“独一无二”的情感落到实处,真挚动人。
编辑提示
文学创作是一场精益求精的修行,难免存在疏漏。若您在阅读中发现错字、语病、逻辑或抄袭问题,又或是作者自身想要修改完善作品,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您的每一条反馈,都是帮助作品日臻完美的珍贵助力,期待与您共筑优质内容。
编辑:黄萍
二审:刘娟丽
三审:李艳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