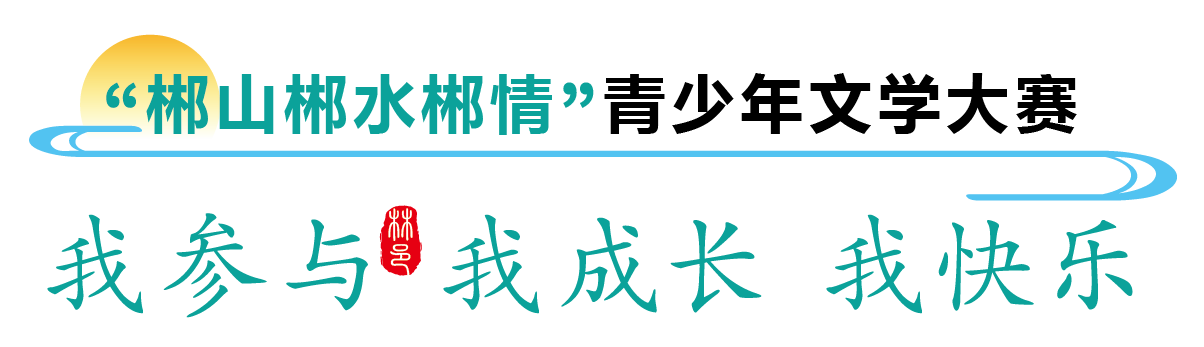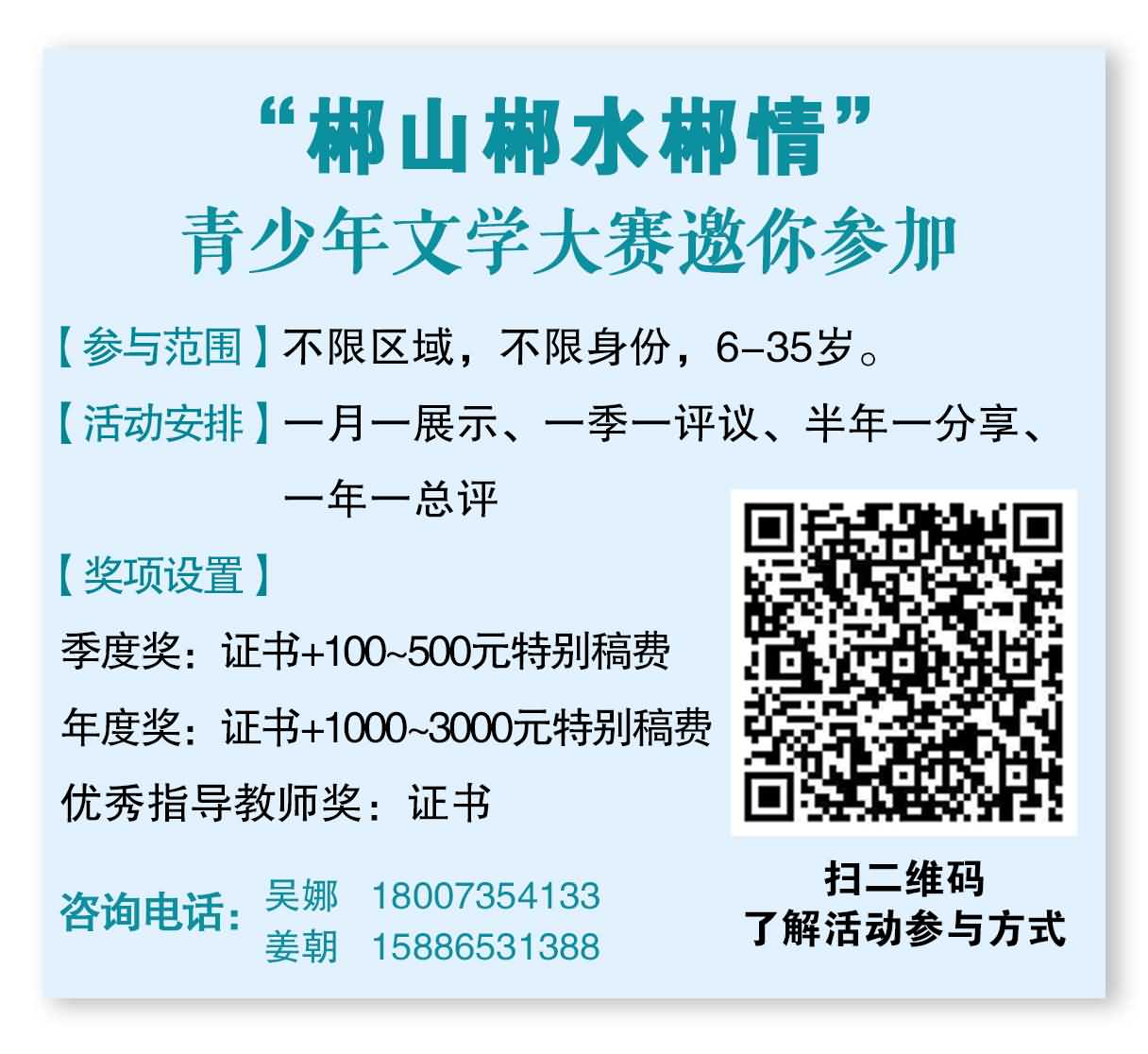邓思羽
郴州市第一中学学生
作者简介
邓思羽,女,2008年8月出生,目前就读于郴州市第一中学,喜好观察生活,善于联想。
创作背景:郴州山水是作者心心念念的惦念,这里,不仅是她的家乡,更是梦想启航的地方。
代表作品
水墨郴州
参赛作者:邓思羽(郴州市第一中学)
指导老师:侯茂红(郴州市第一中学)
郴州的雨,总带着点水墨的性子。不是江南那种绵密到化不开的烟雨,也不是北方急骤的雷阵雨,它像一支蘸了淡墨的羊毫,在清晨或午后,轻轻扫过东江湖的水面,扫过苏仙岭的石阶,扫过板梁古村的黛瓦,于是整座城就晕染开了,成了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。
我总觉得,上帝创造郴州时,定是偏爱用墨的。不然怎会有东江湖那般的雾,浓得像宿墨,淡得像飞白。凌晨五点的东江湖,是这幅长卷的开篇。渔船未动,渔网未开,雾却先醒了。起初是一缕缕,从水面下钻出来,像砚台中刚化开的墨丝,袅袅娜娜地向上飘。渐渐地,墨丝织成了墨绸,整片湖都被裹了进去。远处的山成了浅灰的轮廓,像用侧锋扫出的皴笔,若隐若现;近处的水和雾融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水哪是雾,只觉得脚下的栈道都浮了起来,人站在上面,像踩在一幅未干的画里。
待得朝阳升起,雾便有了层次。先是靠近水面的雾,被染成了淡淡的金,像在墨色里掺了朱砂;再往上,是乳白的雾,像宣纸的底色;最远处的雾,依旧是青灰的,和天空连在一起。这时渔船划过来了,渔夫站在船头,举起渔网——那渔网是橙红色的,在墨色的雾里,像一点醒目的朱膘。网一撒开,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,墨色的背景里,这道弧线就有了筋骨,像书法里的“撇”,有力,却又带着几分飘逸。网落进水里,溅起的水花,是墨滴落在宣纸上晕开的小点,转瞬即逝,却让整幅画有了生气。
从东江湖往西南走,便是苏仙岭。如果说东江湖是一幅淡墨山水画,那苏仙岭就是一幅浓墨的“竖轴”。山不高,却陡,石阶是青石板铺的,被岁月和雨水磨得发亮,像墨锭在砚台上磨出的光泽。石阶两旁的树,枝桠交错,遮天蔽日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,在石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像墨汁滴在纸上,有的地方浓,有的地方淡,有的地方干了,留下一点枯笔。
沿着石阶往上走,会遇到“三绝碑”。碑上刻着秦观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,苏轼的跋,米芾的字,三样都是宋代的珍品,被后人称为“三绝”。石碑立在一个小小的亭子里,亭外是竹林,雨打在竹叶上,“沙沙”作响,像有人在轻轻拂拭这幅墨宝。我站在碑前,看着那些早已模糊的字迹,忽然觉得,秦观当年写下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”时,心里定是积了一肚子的墨——那墨里有失意,有乡愁,有对人生的迷茫。而苏轼和米芾,用他们的笔,给这墨色添了几分豁达。如今,石碑上的墨色淡了,但那份藏在字里行间的情绪,却像墨一样,渗进了苏仙岭的石头里,渗进了每一个来这里的人的心里。
苏仙岭的顶,是苏仙观。观里的道士,穿着青色的道袍,像墨画里的人物。他们扫地、煮茶,动作很慢,像墨在纸上晕开的速度。我在观里喝了一杯茶,茶是山茶,水是山泉,喝进嘴里,有点苦,却又带着几分清甜,像墨的味道——初尝是涩的,细细品,却有回甘。站在观前的露台上往下看,整个郴州城都在脚下。城里的房子,像一个个小小的墨块,散落在山水之间;城里的路,是灰色的,像墨线画的“界行”;远处的河流,是银色的,像墨画里的透气的“白”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郴州的城,本就是一幅墨画,而苏仙岭,就是这幅画的“题跋”,点出了整座城的韵味。
从苏仙岭下来,往东南走,便是板梁古村。如果说东江湖是“水墨”,苏仙岭是“墨笔”,那板梁古村就是“宣纸”——一张被岁月浸染的老宣纸。古村的房子,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,白墙已经泛黄,像宣纸放久了的颜色;黛瓦是深灰色的,像墨锭的颜色。房子的屋檐,都是飞檐翘角,像书法里的“钩”,灵动,却又不失稳重。
村里的路,是青石板铺的,有的地方已经裂了缝,缝里长着青苔,像墨画里的“点苔”,给单调的石板路添了几分生机。路边的巷子,很窄,两个人并排走,需要侧身。巷子的墙上,爬满了牵牛花,紫色的花,绿色的叶,像在宣纸上点了几笔彩墨,却一点也不突兀,反而让整个古村显得更有活力。
我在村里逛的时候,遇到了一位老人。老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,手里拿着一个针线笸箩,正在缝衣服。我问她,村里住了多久了,她说,一辈子了,从出生到现在,就没离开过。她说的时候,嘴角带着笑,像墨画里的人物,平静,却又充满了故事。老人还告诉我,村里的房子,都是祖上传下来的,有的已经有几百年了。
离开板梁古村的时候,天又下起了雨。雨不大,像牛毛,像花针,落在古村的黛瓦上,落在青石板上,落在老人的头发上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古村,有点模糊,却更有韵味。
东江湖的雾在飘,苏仙岭的树在摇,板梁古村的老人在笑,还有那雨,在轻轻地下着,下着……我忽然觉得,郴州的美,就像墨一样,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,需要慢慢品,细细尝,它是含蓄的,是内敛的,是藏在骨子里的。东江湖的雾,苏仙岭的树,板梁古村的瓦……都是这幅水墨郴州的一部分。它们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着郴州的韵味——那是一种安静的、从容的、带着几分禅意的韵味。这种水墨韵味,越品越悠长。
遇见郴州:在山水间藏匿的千年宝藏
参赛作者:邓思羽(郴州市第一中学)
指导老师:侯茂红(郴州市第一中学)
人杰地灵的郴州,是生我养我的故乡。我是她的“孩子”,她是我的“母亲”。这里的山水向来大方,将晨雾的柔软、湖水的清亮、红岩的温润,连同老人们讲了千年的故事,一并揉进了这湘粤交界的山窝窝里,铺成了一幅能摸得着温度的东方长卷。
若说郴州最勾人的惦念,当属第十八福地——苏仙岭。怀揣着高考顺利的心愿,我来到苏仙岭山门前,朱红大门上磨得发浅的纹路,仿佛早已等候多时,轻声道:“进来看看吧。”一脚踏入,如同穿过了一层用时光织就的薄纱。晨雾还未散去,软乎乎的绕在枝头;空气里混着青草和绿叶的气息,每一口都是山林偷偷赠予的清甜。青石板台阶上潜伏着晨露,踩上去滑滑的,需得时刻留着神儿,青苔则顺着石缝往外钻,给老台阶绣了一圈绿边儿。这座福山,将神话故事抽成丝,用千年薄雾织成茧,把郴州的神秘与温柔,细细地包裹其中。山雾有自己的心思,绕着老松树转圈圈;石碑上的字藏着故事,留下岁月品读的痕迹。我顺着台阶慢慢走,每一步都像踩在时光的褶痕里,树上祈福的红绸被风吹得晃悠,好像替山回应着每一个真挚的愿望。
若论郴州最惊艳的景致,东江湖必是翘楚。每当晨雾漫过湖面时,那片水域就成了天然的画布。薄得像纱的雾铺在水上,一会儿聚成软软的棉团,一会儿散成飘扬着的丝带,东江湖仿佛蒙着面纱的舞者,眉眼间尽是温柔与妩媚。世界仿佛都被按下了静音键,只余雾珠滴落湖面的微响,将天地都裹进这片朦胧的柔软里。忽然,一艘小舟自雾中缓缓滑出,令人不禁想起《赤壁赋》中的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之境。渔夫立于船头,手臂一挥,渔网便在空中舒展开一道优美的弧线,溅起的水花在晨光中闪烁细碎的金芒,瞬间成了这幅水墨画中最灵动的一笔。等太阳钻破云彩,金光洒向湖面,湖水一下子褪去朦胧,化作了流动的翡翠。岸边的青山、白墙黛瓦的村子,乃至天上的流云,都清晰地倒映水中,随着波纹轻轻荡漾。乘船沿湖而行,经常可以看见有水鸟贴着水面飞,翅膀划的圈儿和船尾拖的浪交织在一起,共奏一曲清清爽爽的歌,风也轻快起来了,裹挟着湖水的沁凉,温柔地拂过脸庞……
若要寻访千年文脉,濂溪书院便是魂牵之处。青灰色的砖墙、翘起来的屋檐、院中的老莲池,无一不在诉说这里不曾断绝的文脉。周敦颐曾在此讲学,他笔下那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莲花,如今仍在池子里静静绽放,花瓣上露珠滚动,仿佛在续讲千年前的道理,润泽着身为学子的我。在书院里走,手掌扶过略显斑驳的木柱,似乎能触到昔日学子伏案苦读的余温,耳畔仿佛传来朗朗书声,将“仁义礼智信”的种子,悄然植入每一位来访者心田。
沙洲村,让我懂了“半条被子”里的温暖与信念。时光缓缓流淌,当年红军和村民共度艰险的故事,早变成了村口老樟树上的年轮,一圈圈记录这岁月的变迁。如今的沙洲村,青砖黛瓦的新房子排得整整齐齐,宽阔的柏油路伸向远方。村口文化广场上,孩童追逐嬉戏,老人闲坐笑谈,欢声笑语传得很远。走进“半条被子的温暖”陈列馆,玻璃柜中那床褪了色的旧棉被,却依然能让人感觉到跨时空的温暖——它不只是一段历史的见证,更是那颗滚烫初心的模样,这份跨越时间的温暖,感染着每一位到访者,让“为人民奉献”的信念,如磐石般坚定地扎根于吾辈心中,提醒着每个人,温暖与信念从来没走远。
若要品味郴州,必是一场舌尖上的惊喜。清晨街巷,栖凤渡鱼粉的香味最是勾人——翻滚的鱼汤泛着金黄,鲜辣的味儿直往鼻子里钻,乳白的米粉在汤里舒展开,配上嫩乎乎的鱼肉、脆生生的花生和爽口的酸菜,挖一勺吃下去,暖意从舌尖传到手脚尖,一下子把早上的凉赶走了,也给新的一天攒满了劲儿。临武鸭更是郴州味道的代表,用秘制卤料浸过之后,鸭皮亮亮的,肉嚼着紧实,咸香里带着点儿甜,不管是端上桌当菜,还是装在真空包中当礼物,都让人无法忘怀。等瓜果熟了的时候,永兴冰糖橙就是最甜的礼物,剥开橙皮,果肉亮晶晶的,放进嘴里一咬,橙肉就在嘴里炸开,甜得像蜜的汁水在嘴里四溢;东江湖蜜橘带着湖水的清冽,皮薄得像纸,果肉满当当的全是汁,一口一个,清爽的味儿让人停不下嘴。
从苏仙岭的雾中秘境到东江湖的水墨风光,从濂溪书院的千年文脉到沙洲村的红色记忆,从街头巷尾的烟火风味到山野村落的古朴风情,郴州就像一本被时光浸软的厚书,每一页都藏着没想到的惊喜。在这里,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,变得绵长而柔软;山水不再是冰冷的景致,而是带给温暖与欢愉的挚友。每一次和郴州相遇,都是一场跨了千年的浪漫——遇见它的雾,遇见它的故事,也遇见藏在山水褶子里,那个又暖又厚重的郴州。
郴山郴水映归程
参赛作者:邓思羽(郴州市第一中学)
指导老师:侯茂红(郴州市第一中学)
二叔是三十年前从郴州的山坳里走出去的。奶奶以前告诉我,那年他二十出头,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褂子,背着连夜蒸的红薯,站在村口那棵老樟树下,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郴山,说要去广州闯闯。村里人都说他有志气,只有奶奶抹着眼泪,塞给他一个装着山茶的布包:“累了就回来,山里的茶,解乏。”
二叔走的那天,天刚亮,郴江的水泛着青灰色的光,几只白鹭贴着水面飞,翅膀沾了晨露,看着沉甸甸的。他没回头,步子迈得又大又急,像是怕一回头,就被这山这水勾住了脚。
一
二叔在广州混得风生水起。他先是在建筑工地搬砖,后来跟着一个包工头学做装修,再后来自己开了家装修公司,据说手下管着几十号人。每年春节,他都会寄钱回来,有时还会寄些城里的稀罕物——给爷爷的老花镜,给奶奶的呢子大衣,给我的电子表。村里人见了我爷爷,都羡慕地说:“你家老二,在城里当大老板了!”爷爷听了,手里的烟袋锅子敲得“笃笃”响,嘴上却说不出话。
可二叔很少回来。起初是说忙,后来又说公司离不开人,再后来,连春节的电话都变得简短。奶奶每次接完电话,都会坐在门槛上,望着村口的老樟树发呆,手里的针线活停半天,才叹口气:“你二叔,怕是在城里扎根了。”
那年奶奶病重,他终于回来了。那天我放学回家,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。一个穿西装、系领带的男人站在堂屋中央,头发梳得油亮,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。他看见我,笑着向我招手。
我怯生生地看着他,觉得他既熟悉又陌生。他的口音变了,带着城里人的腔调,说话时总不自觉地抬手看手腕上的手表。吃饭的时候,爷爷端上刚蒸的腊肉、炒的蕨菜,还有从郴江里捞的小鱼干。二叔拿起筷子,夹了一块腊肉,嚼了两口,眉头皱了皱:“这腊肉太咸了,城里现在都吃清淡的。”爷爷的手顿了一下,把盘子往他面前推了推:“你小时候最爱吃,说咸香下饭。”二叔没说话,又夹了一筷子蕨菜,嚼了嚼,放下了筷子:“这菜,看着粗糙。”
那天晚上,二叔和爷爷坐在院子里抽烟。爷爷说:“城里再好,也不如家里自在。你看这郴山,晚上能听见鸟叫,早上能闻见茶香,多好。”二叔望着远处的郴山,山影在夜色里黑沉沉的,像一头卧着的老牛。他沉默了半天,才说:“爹,城里有城里的好,机会多。”爹没再说话,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烟,烟圈在月光下慢慢散开,像二叔说的那些城里的事,遥远又模糊。
奶奶去世后,二叔又回了广州。这一次,他走的时候,我和爷爷站在院子里,望着他的车消失在山路尽头,我的心里笼罩着一种莫名的惆怅。
二
二叔五十岁那年,突然回来了。这次他没开车,只背着一个简单的背包,头发白了不少,眼角也有了皱纹,看起来比上次回来老了许多。他站在村口的老樟树下,望着远处的郴山,像三十年前那样,只是这次,他的步子慢了,眼神里多了些疲惫。
“我把公司卖了。”吃饭的时候,二叔突然说。我们全家都愣住了,手里的筷子凝在半空中。“卖了?”爷爷问,“好好的公司,怎么卖了?”二叔笑了笑,夹了一块腊肉,慢慢嚼着:“累了,不想干了。城里的日子,晚上总是睡不着觉。”他顿了顿,喝了一口山茶,茶是今年新采的,带着一股清冽的香气。“还是家里的茶好喝,解乏。”
二叔回来后,就在家里住了下来。他把院子里的空地翻了翻,种上了青菜、辣椒和茄子,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浇水、施肥,像个老农民。爷爷说:“回来干这粗活,干得动吗。”二叔笑着说:“这活不粗,看着菜一天天长起来,心里有劲。”
每天傍晚,二叔都会去郴江边散步。他沿着江边的石板路慢慢走,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,看孩子们在岸边追逐打闹。有时他会坐在江边的石头上,望着远处的郴山,一看就是半天。有一次我问他:“二叔,你在看什么?”他转过头,笑着说:“看山,看水,看这日子。”
村里的人见二叔回来了,都来串门。有人问他:“你在城里那么成功,怎么回来了?”二叔总是笑着说:“家里山水这么好,咋不能回来?”有人又问:“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?就在村里待着?”二叔说:“待着,挺好。这山水,养人。”
三
二叔回来的第二年,村里搞旅游开发,有人看中了村后的那片竹林,想租下来建民宿。村里的人意见不一,有的想租,说能赚钱;有的不想租,说那片竹林是村里的根,不能动。
那天晚上,村里开大会,讨论这件事。二叔也去了。会上,租地的老板说得天花乱坠,说建了民宿,村里的人都能赚钱,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有人动心了,举手表示同意。这时,二叔站了起来,他说:“老板,你说的赚钱,我信。可你有没有想过,这竹林没了,我们去哪里挖竹笋?这山上的树砍了,郴江的水会不会变浑?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山里,靠的就是这山这水。要是为了赚钱,把这山这水毁了,就算赚再多的钱,心里也不安稳。”
他的话刚说完,村里的老人们都纷纷点头。有人说:“老二说得对,这山这水是我们的命根子,不能动。”有人说:“我们虽然穷,但也不能为了钱,把祖宗留下的东西卖了。”最后,大家一致决定,不租那片竹林。租地的老板见没人同意,只好悻悻地走了。
从那以后,村里人觉得二叔不只是城里回来的有钱人。有人说:“还是城里回来的人有见识,知道什么重要。”二叔听了,只是笑着说:“不是我有见识,是这山这水教我的。你在这山里待久了,就知道,什么都比不上心里的踏实。”
四
清明节,我们一家人给奶奶扫完墓后,二叔坐在老樟树下喝茶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布衫,手里拿着一个粗瓷茶碗,慢慢啜着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他的脸上,眼睛泛着血丝,抹去了阑珊的泪痕。
“二叔,你现在觉得,回来值吗?”我问。他望着远处的郴山,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,红的、粉的、白的,像一片彩色的云。郴江的水在山脚下蜿蜒流淌,泛着粼粼的波光。
“值。”他说,“年轻时总觉得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想出去闯闯,想证明自己。可等真的在城里站稳了脚跟,才发现,最想要的,其实就在身边。我说这山水好,不只是好在这山水养眼,看着舒畅,更重要的是这山水养心!我看着这郴山郴水,就想到你奶奶几十年来给我煮的饭、做的菜、泡的茶,这山水还好在一片感情啊!山水在,茶在,一家人在,心便安稳,你说值不值呢?”
二叔顿了顿,又喝了一口茶。他眼角的闪过泪光,阳光仿佛更加明媚。
看着郴山郴水,沉静而踏实,我心里很久以前笼罩的一缕惆怅突然消散。像二叔一样,此刻的山水,就是我的安心处。
作品点评
《水墨郴州》以 “水墨” 为灵魂,将郴州的景致串联成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。东江湖的雾如宿墨飞白,苏仙岭的石似浓墨皴笔,板梁古村若浸岁宣纸,意象精准又灵动。文字兼具画面感与感染力,既以细腻笔触勾勒雨雾、石阶、黛瓦的形态,又借秦观词、古村老人暗抒韵味,将自然景致与人文底蕴相融。行文如墨晕宣纸,层层递进,最终道出郴州含蓄内敛的禅意之美,余味悠长,尽显文字的水墨风骨。
《遇见郴州:在山水间藏匿的千年宝藏》以 “故乡儿女” 的视角,将郴州的山水、文脉、红色记忆与烟火气编织成篇,情感真挚又富有层次感。作者用诗意笔触描摹苏仙岭晨雾、东江湖渔舟,让自然景致兼具灵秀与温度;借濂溪书院莲池、沙洲村老樟,串联起千年文脉与红色初心,古今交融自然。对栖凤渡鱼粉等美食的描写生动鲜活,更添生活气息。全文结构清晰,语言细腻优美,如 “时光织就的薄纱”“山水褶子里的温暖” 等表达,既见文字功底,又满含对故乡的深情,让读者沉浸式感受郴州的厚重与灵动。
《郴山郴水映归程》以 “郴山郴水” 为情感纽带,串联二叔三十年的归程与心路。从年少闯城的决绝,到中年归乡的沉静,人物成长弧光清晰动人。腊肉、山茶、老樟树等细节满含乡土温度,祖孙对话暗藏代际理解与牵挂。最动人处,是二叔归乡后守护竹林的选择,让 “山水养心” 的感悟落地,既写出个人对根的眷恋,更诠释了乡土之于心灵的安顿力量,文字质朴却余味悠长。
编辑提示
文学创作是一场精益求精的修行,难免存在疏漏。若您在阅读中发现错字、语病、逻辑或抄袭问题,又或是作者自身想要修改完善作品,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您的每一条反馈,都是帮助作品日臻完美的珍贵助力,期待与您共筑优质内容。
编辑:李金香
二审:张振萍
三审:吴 娜